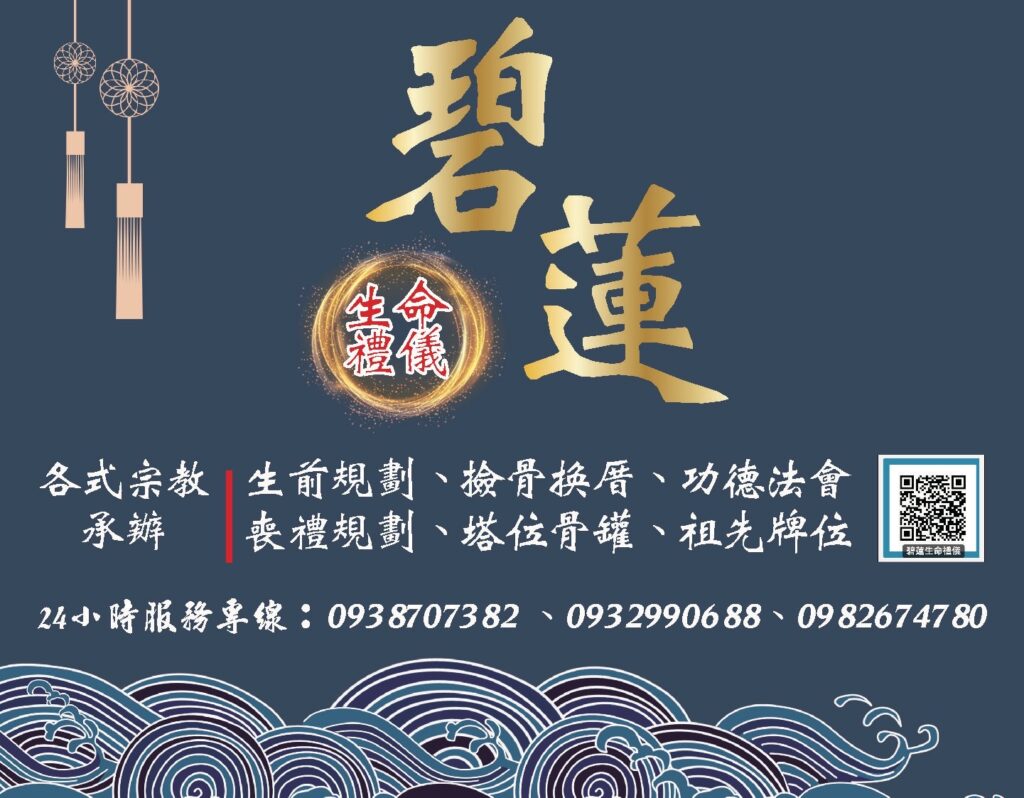「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禮記。昏義》。又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曾子也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都明白揭示喪葬儀式在華人生命禮儀中不可抹滅的價值,廣義而言,「禮」是行動式的儀式性宗教,具備儀式性的展演作用,和宗教的本質,從治療學的角度觀而言,有積極性的治療意義,對個人而言即所謂「轉移作用」與「淨化作用」。對整體社會最終能夠產生「民德歸厚」的效果。
儀式的轉移過程、代罪過程,具有淨化、贖罪的治療功能,使生命中的罪乙愆得以洗滌、苦悶得以淨化、祈願得以實現、靈魂得以昇華。在儀式的神秘一氛圍中,擺脫俗世的不潔,靈魂得以超越凡俗,進入神聖純潔的境地,在俗與聖之間,經歷一場象徵性的生命的死亡與復活。以傳統華人喪葬儀式的沐浴為例,中國喪葬儀式中淨身儀式經神明的答允後,以水淨身,此水因獲河川神祁的加持,是神聖的力量,將往生者一生的罪過洗淨,以便以潔淨之身往生新世界,這是精神上的意義。亦有中國孝道倫理的意義,淨身的同時,子、女、媳參予擦拭身體表示盡最後孝親之禮。實務上,亦是將往生者身體上遺留的藥水,傷口紗布,尿布等除去後做徹底清潔。一方面強化遺體的清潔處理,同時對於強化遺體的保護作用。
傳統華人「淨身」禮儀有兩個重要意義:一是「除穢」,除了將往生者臨終時身體上所可能沾惹的污物與不潔洗淨外,更有將人一生的污穢和原罪徹底洗淨的意義。第二是「迎新」,往生者以聖潔的靈體來面對另一個世界新生命的開始,讓摯愛的親人以潔淨,安祥,尊嚴的畫上此生的句點。這些意涵在長期被忽略,近幾年搭上兩岸殯葬改革的風潮,傳統喪葬習俗的「沐浴淨身」儀式在兩岸逐漸被重視。但也衍生另一個現象—「沐浴淨身」的儀式或是套用日本的「湯灌」,或是演變成商業手法操作下的「大體SPA」!
儀式既具有轉移和淨化的審美功能,個人生命與團體文化在經歷儀式的洗禮治療之後,「接觸」與「溝通」是個人與團體間共同的需要,在人文化成的文明社會中,身體的接觸為最直接、最真誠的溝通方式儀式治療上的意義,「安全感」及「信任感」對於一個曾經在人際關係中受傷的心靈而言,是極為困難的目標。個人一旦能走出創傷,擁抱人群,對於治療工程而言,是莫大的肯定。(林素玟 《儀式、審美與治療~~論(禮記‧樂記)的審美治療》)
將台灣道教傳統喪葬儀式依照Worden(1995/2005) 所提出哀悼的四個主要任務:一是接受失落的事實;二是經驗悲傷的痛苦;三是重新適應一個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四是將對逝者的情感重新投注在未來的生活上等四個任務上來看,某些喪葬儀式的進行確實是有達到某些哀傷階段任務的功能。以臺灣傳統死亡儀式的「牽亡歌陣」儀式為例,用Worden 的「哀悼任務論」為依據來檢視「牽亡歌陣」,就哀悼的四項任務而言,「牽亡歌陣」至少能履行第一項任務:接受失落的事實。和第二項任務:經驗悲傷的痛苦。就悲傷輔導的四個目標而言,「牽亡歌陣」至少能達到第一個目標:增加失落的現實感。第二個目標:協助當事人已表達或潛在的情感。以及第四個目標:鼓勵當事人向逝者道別。就悲傷輔導的使用原則而言,至少可以看見「牽亡歌陣」在喪親家屬身上運用的原刖一「協助生者體認失落」、原則二「幫助生者界定並表達情感」、原則五「允許時間去悲傷」以及原則六「闡明『正常的』的悲傷行為」。因此,以Worden的理論來檢視之,可以確知「牽亡歌陣」對於部份亡者家屬的確具有悲傷輔導的功能。(龔萬候、2006 碩士論文)。
無論是從華人的喪葬儀式研究,或是西方的「哀悼任務論」,死亡儀式無疑是最佳的治療儀式模式,也是被人類保留至今最好的儀式治療;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變遷,死亡儀式也面臨變化的過程,尤其在共產主義興起的年代喪葬儀式成為去儀式化論調首當其衝被提出檢討,而在華人傳統喪葬儀式也同樣面臨「繁文縟節」「封建迷信」的討論聲浪,雖然如此,許多傳統喪葬儀式並沒有因此而完全消失殆盡,因為對華人而言歷年的喪葬儀式,不只是遵循傳統道德,如孝道、慎終追遠、其背後隱含的涵意深受儒家、道家的影響,甚至連民間信仰也受到道教影響,道教乃承襲黃老之學及諸子百家所好而成的宗教,與中華文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後又受到佛教的影響,使得華人傳統喪葬儀式的演變得更形複雜,於是在近二十年兩岸相繼吹起殯葬改革的風潮,華人喪葬喪葬儀式再次地受到探討與檢驗。
台灣傳統喪葬儀式的悲傷輔導效用
由於台灣歷年來的喪葬儀式,不只是遵循傳統道德,如:孝道、慎終追遠等,其背後隱含的涵義深受儒家、道家的影響,並且在民間信仰上又以信奉道教為主,道教乃承襲黃老之學及諸子百家所好而成之宗教,與中華文化共始終,故兩者不可分離。因此在許多的喪葬儀式都深受道教生死觀影響甚鉅。如果一名治療者對於喪葬禮俗不了解,可能會被這些繁文縟節所困擾甚至因為不甚理解而無法對當事人所處文化的喪葬習俗有所包容和體悟;因此去了解目前我們所處的台灣社會中最為盛行的道教傳統喪葬儀式實有助益於悲傷輔導與治療的進行和效果。
若將台灣道教傳統喪葬儀式依照Worden(1995/2005) 所提出哀悼的四個主要任務:一是接受失落的事實;二是經驗悲傷的痛苦;三是重新適應一個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四是將對逝者的情感重新投注在未來的生活上等四個任務上來看,某些喪葬儀式的進行確實是有達到某些哀傷階段任務的功能。以下即是依據Worden 所提出的哀悼任務,加以分析和說明台灣喪葬文化中各種儀式對於哀悼任務完成的助益。在儀式的部份除了筆者融入個人參與喪禮儀式的經驗之外,在禮俗內容的介紹部份大多依據范勝雄(1998)台灣民間的喪葬禮俗一文,有興趣者可更加進一步了解和參考。以下即進入本人所整理和歸納在哀傷復原階段任務中,相關儀式的說明和介紹。
一、接受失落的事實
哀傷的第一項任務,就是要去接受死亡已發生的事實,在儀式上有很多作為都有助於生者去體驗和接受逝者巳矣這個事實。
(一)拼廳與舖水舖
病人自知將終,皆會指定以大廳為其「正終」之所,因此病人危急之前,子孫應先將大廳打掃乾淨,準備舖放水舖,俗稱「拼廳」。拼廳後即要舖水舖,以厚木板一張(六尺長三尺寬左右)用椅子墊高置於廳旁,勿緊靠牆壁,男移龍方(進門之右方),女移虎方(進門之左方),或以神明牌位之方向,男左女右,頭裡腳外。
(二)為死者更壽衣
人死穿以入殮的衣服稱為「壽衣」,當病人危急之前,家屬即應為他準備好。台灣地區之習俗,壽衣算層而不算件(即上衣有裡子即兩層),上衣通常是六件七層,褲子二件至三件,白襪黑布鞋。
(三)遮神
病人以大廳為正終之所,大廳供奉有神明、祖先,一旦氣絕,要沐浴、更衣等,怕對神明祖先不敬(俗稱見剌)必須用米篩或紅紙遮住神明及祖先牌位,俗稱遮神,大殮入棺後再除去。
(四)隨侍在側
病人移至大廳水舖之後,子女即必須隨侍在側,不可單獨留病人在大廳,以免病人去世不知是幾時嚥氣,徒留遺憾。
(五)舉哀
病人一旦斷氣死亡,依俗須於門口焚燒一頂紙轎(車)供靈魂乘用,俗稱「燒魂轎」以大碗公為香爐,焚香拜亡靈,全家大小始舉哀慟哭,儒家重視人倫感情,故以哭泣辟踊以盡其哀,然而佛教界人士則以為死者去世八小時之內,意識未完全脫離形體,子孫不可移動,不可哭泣。
(六)易枕與蓋水被
子孫用石頭或一支大銀紙做為屍枕,傳說如此子孫才會「頭殼硬」(聰明之意),實則將頭墊高後屍首才會收下巴,不致張口嚇人,而且較不易腐臭。屍身棉被須去除,改罩水被(一大塊白布中綴紅布),用意除覆其形外,也是避免蓋棉被容易發臭。
(七)陳設腳尾物
腳尾處依俗須陳列腳尾飯一碗(露天炊煮),用大碗盛滿,越滿越好,飯上放一粒熟鴨蛋並正插一雙竹筷,供死者享用以便上路,另置腳尾火(油錡仔)、腳尾爐(用碗公盛砂做香爐),並燒腳尾紙(小銀),供死者做盤纏,應慢燒,以免室溫升高。
(八)變服
初終尚無孝服,唯為宜悲誌哀,全身改穿素色衣服。
(九)帷堂與闔扉
惟堂俗稱「吊九條」,即以一全匹白布,用竹竿架吊起,彎九次後將屍床圍起來,目的在隔開內外;同時須將門扉關一扇,以防日月光照射到屍身上。
(十)門外示喪與鄰人掛紅
家有喪事應於門外張貼告示,以白紙黑字寫明「嚴制」或「慈制」或「喪中」(長輩尚在,晚輩去世時用之)。紅色春聯應以撕除。為敦睦鄰居,應為附近鄰居大門貼一塊紅紙,以示吉凶有別。紅紙於出殯日啟靈後始撕除,並由道士洗淨,貼上淨符。
(十一)守舖與關貓:
親人死後,子孫哀慟不忍,必須小心看守,孝男夜則席地而眠,稱為「守舖」,守舖除了哀傷親人之死不忍離開寸步之外,尚可預防親人因休克「死亡」復活而乏人急救,有親友來弔唁時不致無人照應,同時也防止肉食性貓科動物之毀損屍體。
(十二)請人買布料、製(租)孝服與孝誌
喪事所用布料以白布為最多,孝服若是自製,則須採購五服(麻苧、藍、黃、紅)布料。
(十三)擇日與辦理死亡登記
喪事重忌諱,入木(大殮)、轉柩、落葬等均須選日選時。一般是先看入木時辰,然後才看墓地,後再看出殯之時日。家屬持死亡證書向戶政事務所辦理死亡登記,始能入殮。
(十四)報喪
入木時辰看好便可報喪,父喪要報伯叔、姑母等,母喪則要通知外家俗稱「報白」,母舅以外的親戚,可以拜託他人代為報喪,或用電話通報。
(十五)買棺
俗稱「買大厝」,父喪由伯叔一人陪孝男去,母喪由外家一人陪孝男去,另外可請一位懂木材之鄰友作陪。棺木,土葬與與火化所用不同。
(十六)宗教法事
初喪未入殮請道士或僧尼唸經,稱「唸腳尾經」;或者俟入殮時再一併舉行,稱「入木法事」。
(十七)辭生
此為尚看得見死者容貌最後一次之祭奠,也是死者辭別「生人」階段最後一次祭奠,故名「辭生」。須準備六至十二碗食碗,陳於死者面前,長子站在竹椅子,餘人跪於屍旁,由道士或土公用竹筷代死者夾菜每夾一道便唸一道吉利話。
二、經驗悲傷的痛苦
在接受死亡和失落的事實之後,第二項重要任務就是要能夠充份去經驗悲傷所帶來的痛苦,因為若是生者逃避或壓抑痛苦的事都反而會延長痛苦。因此下列儀式可以用來幫助達成這項任務:
(一)哭路頭與奔喪
出嫁女兒聞耗喪回家,離家一段距離即須號哭,且有哭辭,聲極淒洌,俗稱「哭路頭」。凡長輩嚥氣時未隨侍在側之子孫,自外地奔喪回去,必須匍匐入門,表示自己不孝,奉養無狀。
(二)做孝
是表達哀傷的一種儀式、是哭泣的行為,在移棺或弔者,尤其是長輩來憑弔時,除了焚香外,通常都會有女眷在旁做孝。
(三)哭棺材頭
是指出殯前,喪家親人穿著喪服倚棺而哭。
三、重新適應一個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將對逝者的情感重新投注在未來的生活上因為這兩項任務的主要目的,是為適應逝者不存在的事實以及生者在外在角色及內在心理上的調整和變化;並且能夠重找到生命的意義及目標。此外,在與逝者的連結上,並不是促使生者放棄與逝者的關係,而是能夠為逝者找到一個處所,使生者能和逝者連結,但不會阻礙生者繼續生活。因此下列儀式的作用即是有此兩項功能:
(一)乞手尾錢
「辭生」後即乞手尾錢,把預放在死者衣袋內的硬幣分給子孫,每人一枚,用白布或藍布穿孔繫於手腕,父死繫於左手,母死繫於右手,帶至換孝為止,象徵死者愛護子孫,留下財產分給眾子孫,另一方面也象徵著責任之傳承。
(二)落葬
指在下葬時道士會唸一些吉祥話,而親屬則應聲喊:有喔…等。
(三)做百日
逝世當天算起一百日所做之祭祀,應舉哀,稱「做百日」,子孫於滿七未
換孝者,是日須換孝。部份地區亦有提前做百日,即依男兒的人數加上長孫,由「百日」的日數扣除之。
(四)做對年(小祥)
逝世一週年所做的祭祀,應舉哀,稱「做對年」逢閏年則提前一個月,子孫親友到墓地,家中或利用公共場所舉行追悼會,稱為「祭禮」。孫輩帶孝一年,是日脫孝,換紅毛線帶三日後即除去。
(五)合爐
即把魂帛燒掉並將其名字寫在祖先牌位上,將爐灰取一小部分至祖先香爐中,叫「合爐」。合爐古代在二十五個月時舉行,現今改為對年後選擇一吉日為之,有的其至在「對年」當天行之。
(六)培墓與掃墓
親墳完墳後三年內要「培墓」:子孫須要備酒餚、三牲五果祭拜第一年開墓頭要在清明前擇一日,第二年在清明當天,第三年在清明後擇一天。此後每年在清明前後率子孫帶水果冥紙去掃墓。
(七)新忌、做忌
即「逝世」後第二次逝世紀念日,此後年年以此日做忌日。
(八)撿金(撿骨、洗骨)
「撿金」本為古代幾個少數民族及地區所特有的現象,台灣地區由於移民社會的特性,加上氣候等因素,葬後若干年開棺洗骨,將骨骸另裝在一只陶甕中,安奉於納骨塔。
有別於歐美社會,漢民族文化的歷史起源甚早,號稱擁有超過五千年的人類文明史,所保留延用的各類儀式更多於其他民族,而臺灣更是經歷過西班牙,荷蘭,日本的統治,或多或少在社會儀式被影響,但是在死亡儀式上卻仍然保有漢人民族的傳統思想,這些傳統思想在喪葬儀式的過程很難被清楚界定與信仰有關,有時會被歸類成風俗或是所謂的民間信仰,例如牽亡陣此類喪葬藝陣。
因此,台灣傳統死亡儀式從臨終,初終,入殮,家公奠禮,安葬到返主歸陰,其中還有經懺法事這類信仰儀式,所有過程涵蓋臨終關懷,悲傷撫慰和後續關懷的療癒效果,這種療癒效果呈現出儀式治療的悲傷處遇功能。
(本文摘錄自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鍾美芳老師發表於台灣諮商季刊)
殯葬禮俗的儀節流程與設計,實際上是人們長期面對死亡挑戰而來的智慧與行動的累積,是比醫學更為古老的生存對應法則,屬於生命禮儀的一部分,或者可以算是臨終精神醫學的源頭或前身,在尚未有醫療的相關知識時,人們已重視生命本質的探討與追求,理解到死亡是人生的必經之路,體驗到唯有經歷死亡才能彰顯出生命存有的意義與價值,衍生出一系列與死亡相關的殯葬儀式。這些儀式是具有著極為深刻的生命象徵意涵,在處理死亡與死後的相關事宜中,用來安頓亡者與生者共同承擔瀕死的歷程來接受死亡的考驗,每一個儀節的背後都帶有著精密構想的巧思,是建立在長久生命體驗下的普遍情感共識,要求當個體生命走過從有到無的各個階段時,是需要有一整套綿密繁複的儀式來幫助人們安然度過生命的重要關卡(殯葬禮俗的儀式治療功能, 鄭志明 空大出版社)。
引用謝雯嬋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2004碩士論文「佛教助念對喪親者悲傷療癒影響之探討」,由研究結果可知受訪者經由佛教助念產生了「傳遞」、「支持」、「跨越」、「改變」、「持續」、「轉變」等之經驗歷程模式,呈現相互影響非直線式關係,在經驗歷程中原有之悲傷經驗皆產生了轉變。
在分析佛教助念對於悲傷療癒之助益歸結有幾點:
1、 佛教助念儀式對於親人死後去處的解說及引導形成一個「可以想像的死後存在」,幫助對於親人「生死意象轉換」維持關係連結,儀式導引之生死信念如「死亡不是永遠的結束」、「分離是短暫的」、「有再相聚的一天」,給予喪慟中希望與支持。
2、 佛教助念儀式的引導及念佛過程給予了一個幫助親人的方法及生死情感傳達的通道,跟隨著助念人員引導「往生」的過程,令喪親者原有「親人死亡」的悲傷轉換成「親人即將往生到一個很美好地方」的心像支持。
3、 助念儀式歷程中助念人員無私的付出與陪伴,亦提供了喪慟中的社會支持。
4、 助念儀式的力量提供了安定與轉念力量、神聖的庇護力量、救渡的感應安慰(如遺體之安祥或夢境呈現),提供喪慟中支持及安慰。
5、 助念歷程中的念佛持誦經文迴向的引導方式亦提供了一種社會學習的模仿方式,喪親者能跟隨著行持,甚至延續在助念結束後,繼續成為幫助親人及自身調適悲傷、安定內心的一個方式,亦即佛教助念於喪親者的悲傷療癒歷程扮演一道從「失落的死亡世界」到「希望的彼岸世界」連結與轉換的橋樑。
受訪者在經歷佛教助念後除了原來悲傷經驗轉變外,原有之生命亦產生了轉化,如:生命哲理有了啟發,生命觸角亦能延伸到自我生死的反思層面,產生回饋付出之心去服務他人,在服務過程中有了自我成長,生命視野也擴大了,同時在逐步走出悲傷之後,亦能為親人的離逝尋求意義,終究步上療癒之路。
殯葬禮俗源自古老的靈魂觀念與原始宗教,是早期先民們在現實生存環境中追求精神優化的生命實踐,經由後代儒家、道教與佛教等思想與儀式的擴充,更加強化殯葬儀式的意義治療功能,從觀念的建構到行為的活動,都帶有豐富神聖體驗的終極信念,融入到社會群體約定俗成的習俗之巾,是集體文化意識下的精神教養,提升人們的心靈境界來對應死亡的各種存有挑戰(殯葬禮俗的儀式治療功能, 鄭志明 空大出版社)。